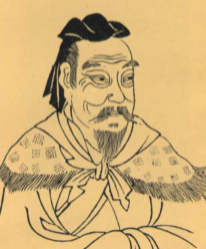纠错
人物生平
严光本姓庄,后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其姓,一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
建武元年(25年),刘秀建立东汉,严光于是隐名换姓,隐居在桐庐富春江畔,每日垂钓,后此地为桐庐严子陵钓台。刘秀思贤念旧,就下令按照严光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齐地报称有一男子披着羊裘在泽中垂钓,刘秀怀疑那就是严光,即遣使备置安车、玄纁,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
司徒侯霸与严光是老相识,派人送信给严光。送信的人便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到了,一心想立刻就来拜访,限于朝廷的有关制度不便,所以不能来。希望能在天黑后,亲自来向你表达歉意。”严光不说话,将书简扔给送信的人。口授说:“君房先生:官位到了三公,很好。怀着仁心辅助仁义天下都高兴,拍马屁看人脸色办事可就要身首异处了。”侯霸收到信看过,封好了再上奏刘秀。刘秀笑着说:“这狂家伙还是老样子。”当天就亲自来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睡着不起来,刘秀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呀!子陵,就不能相帮着做点事吗?”严光又睡着不讲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看了好一会,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刘秀说:“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上车,叹息着离开了。
后来,刘秀又请严光到宫里去,谈说过去的交往旧事,两人在一起相处好多天。一次,刘秀随意地问严光:“我比过去怎么样?”严光回答说:“陛下比过去稍稍有点变化。”说完话便睡在一起。严光睡熟了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冲犯了帝座,很厉害。刘秀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后授谏议大夫,严光不肯屈意接受,于是归隐富春山(今浙江省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
建武十七年(41年),朝廷一次征召他,严光仍不就。严光八十岁时,在家中去世。刘秀倍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
建武元年(25年),刘秀建立东汉,严光于是隐名换姓,隐居在桐庐富春江畔,每日垂钓,后此地为桐庐严子陵钓台。刘秀思贤念旧,就下令按照严光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齐地报称有一男子披着羊裘在泽中垂钓,刘秀怀疑那就是严光,即遣使备置安车、玄纁,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
司徒侯霸与严光是老相识,派人送信给严光。送信的人便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到了,一心想立刻就来拜访,限于朝廷的有关制度不便,所以不能来。希望能在天黑后,亲自来向你表达歉意。”严光不说话,将书简扔给送信的人。口授说:“君房先生:官位到了三公,很好。怀着仁心辅助仁义天下都高兴,拍马屁看人脸色办事可就要身首异处了。”侯霸收到信看过,封好了再上奏刘秀。刘秀笑着说:“这狂家伙还是老样子。”当天就亲自来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睡着不起来,刘秀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呀!子陵,就不能相帮着做点事吗?”严光又睡着不讲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看了好一会,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刘秀说:“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上车,叹息着离开了。
后来,刘秀又请严光到宫里去,谈说过去的交往旧事,两人在一起相处好多天。一次,刘秀随意地问严光:“我比过去怎么样?”严光回答说:“陛下比过去稍稍有点变化。”说完话便睡在一起。严光睡熟了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冲犯了帝座,很厉害。刘秀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后授谏议大夫,严光不肯屈意接受,于是归隐富春山(今浙江省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
建武十七年(41年),朝廷一次征召他,严光仍不就。严光八十岁时,在家中去世。刘秀倍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
展开阅读全文 ∨
纠错
人物评价
范晔: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权徳舆:绝顶耸苍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灵栖颢元,缨冕犹缁尘。不乐禁中卧,郗归江上春。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报故人。则知大贤心,不独私其身。弛张有深致,耕钓陶天真。奈何清风后,扰扰论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纷纶。我行访遗台,仰古怀逸民。矰缴鸿鹄远,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穷,山色凌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辉照无垠。
梁肃:当哀平之后,天地既闭,先生韬其光,隐而不见建武,反正云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乱之际,卷舒夷旷之域,如云出于山,游于天复,归于无间,不可得而累也,则激清风耸,高节以遗后世,先生之道可见。
吴筠:汉皇敦故友,物色访严生。三聘迨深泽,一来遇帝庭。紫宸同御寝,玄象验客星。禄位终不屈,云山乐躬耕。
罗隐:岩岩而高者,严子之钓台也。寥寥不归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苍。苔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贱莫贱于布衣。龙争蛇蛰兮,风雨相遗。干戈载靡兮,悠悠梦思。何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故得脱邯郸之难,破犀象之师,造二百年之业,继三尺剑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亲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乎!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范仲淹:①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②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梅尧臣:不顾万乘主,不屈千户侯,手澄百金鱼,身被一羊裘。借问此何耳,心远忘九州。青山束寒滩,溅浪惊素鸥。以之为朋亲,安慕乘华輈。老氏轻璧马,庄生恶牺牛。终为蕴石玉,敻古辉岩陬。
王安石:汉庭来见一羊裘,闵默还归旧钓舟。迹似蟠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岂能留。崎岖冯衍才终废,寂寞桓谭道被尤。回视苍生终不遇,脱身江海更何求。
陈鉴之:渭滨一叟发垂素,西伯与之无雅故。幡然为舍钓鱼竿。八极风云生指顾。先生少与文叔游,眼看日角兴炎刘。胡为掉头不肯住,垂纶依旧披羊裘。周文虚已师贤哲,光武规模欠宏阔。三公清坐台阁尊,先生回首桐江月。桐江月色无古今,白波苍嶂幽人心。
范成大:浮生有几,叹欢娱常少,忧愁相属。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燕蝠尘中,鸡虫影里,见了还追逐。山间林下,几人真个幽独。 谁似当日严君,故人龙衮,独抱羊裘宿。试把渔竿都掉了,百种千般拘束。两岸烟林,半溪山影,此处无荣辱。荒台遗像,至今嗟咏不足。
杨万里: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张轼:考子陵之言论风旨,亦非索隐行怪必欲长往而不返者。彼与光武少而想从,知其心度最为详也。以治谓光武欲为当时之治,则当时之治,则当时之人才固足办之,而无待乎已也。若欲进乎两汉之事,则又惧有未能信从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其尊礼之虚名,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宁不就之。
钱时:污浊成风,节廉道丧,鼓一世于浮竞之途,贪荣冒而不知耻,于是而有人焉脱身势利,高蹈林泉,优游恬退以终其身,虽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未必合圣人之中道,而风节凛凛足以激颓波,厉污俗,此严光、周党之徒,后世犹有取焉。
徐钧:故人风谊可态忘,辞禄无嫌故态狂。仁义一言非小补,此身何必佐岩廊。
郑锐:先生少与光武同学,熟知光武为人,其曰“差增于往”盖有以觇其衷,度其后居无何,后废子易,不能保骨肉之爱,而何有于微时一布衣交。此则揣摩未形之恶,捐弃生平之好,非君子长者事,而先生忍为之呼?
宋濂(《苍云轩铭》):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为尽力。子陵何隐而不出,既出而决去哉?盖光武察察自用,其后宰辅多不以礼退,子陵预知其如此,故决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旧之义。此子陵所以为高也。苟徒以隐为高也,孰不可为子陵哉?
方孝孺: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李昌祺:桐江连天兮秋水长,富春摩空兮烟树苍。客星兮寒芒,汉宫兮苔荒。彼争攀龙鳞兮铭勋旗常,此宁着羊裘兮垂纶沧浪。以足加腹兮忱故态之犹狂,亷贪立懦兮掲世之防。云台钓台兮其髙颉颃,二十八人兮图像已忘,先生万古兮岿祠堂。
何孟春:春观子陵与侯君房书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得书奏帝,帝有“狂奴故态”之哂,及幸其馆,抚腹之问,声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岂礼貌贤者之言也。子陵是时年亦已长矣,帝不以师友处子陵,而职谏议大夫之除,何哉?使子陵而职谏议大夫,不能一毫阿谀顺旨,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则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政归台阁,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群臣往往以非谶而见罢黜,将来之事废后易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时有死其职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职,非贤者所以爱其君之初意,去其君受职之余,孰与今日之不受之为全其节,而君臣之间两可无憾也哉!呜呼,此子陵之心也!
徐渭: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袁宏道:因山以为台,因水以为滩,因草以为丝,因木以为竿,因拙而辞世,因傲而弃官。严翁诚自知,刘叔亦难瞒。宁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郭子章:严光加足于帝腹,光忘帝之贵也;唐肃宗因李泌假寐,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帝自忘其贵也。布衣之遇天子,至光、泌极矣。桐江一丝,扶汉九鼎;历佐四圣,而后脱屣。光、泌所以报人主者,亦至矣哉。
王夫之:矫厉亢爽,耻为物下,道非可隐,而自旌其志,严光、周党是也。
李光地:①古来高隐人,不尽是忘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严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②子陵高风峻节,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厉天下之人心。东汉末,宦祸、党锢频兴,而赴仁蹈义者,视死如归,子陵之力也。
权徳舆:绝顶耸苍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灵栖颢元,缨冕犹缁尘。不乐禁中卧,郗归江上春。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报故人。则知大贤心,不独私其身。弛张有深致,耕钓陶天真。奈何清风后,扰扰论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纷纶。我行访遗台,仰古怀逸民。矰缴鸿鹄远,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穷,山色凌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辉照无垠。
梁肃:当哀平之后,天地既闭,先生韬其光,隐而不见建武,反正云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乱之际,卷舒夷旷之域,如云出于山,游于天复,归于无间,不可得而累也,则激清风耸,高节以遗后世,先生之道可见。
吴筠:汉皇敦故友,物色访严生。三聘迨深泽,一来遇帝庭。紫宸同御寝,玄象验客星。禄位终不屈,云山乐躬耕。
罗隐:岩岩而高者,严子之钓台也。寥寥不归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苍。苔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贱莫贱于布衣。龙争蛇蛰兮,风雨相遗。干戈载靡兮,悠悠梦思。何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故得脱邯郸之难,破犀象之师,造二百年之业,继三尺剑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亲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乎!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范仲淹:①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②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梅尧臣:不顾万乘主,不屈千户侯,手澄百金鱼,身被一羊裘。借问此何耳,心远忘九州。青山束寒滩,溅浪惊素鸥。以之为朋亲,安慕乘华輈。老氏轻璧马,庄生恶牺牛。终为蕴石玉,敻古辉岩陬。
王安石:汉庭来见一羊裘,闵默还归旧钓舟。迹似蟠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岂能留。崎岖冯衍才终废,寂寞桓谭道被尤。回视苍生终不遇,脱身江海更何求。
陈鉴之:渭滨一叟发垂素,西伯与之无雅故。幡然为舍钓鱼竿。八极风云生指顾。先生少与文叔游,眼看日角兴炎刘。胡为掉头不肯住,垂纶依旧披羊裘。周文虚已师贤哲,光武规模欠宏阔。三公清坐台阁尊,先生回首桐江月。桐江月色无古今,白波苍嶂幽人心。
范成大:浮生有几,叹欢娱常少,忧愁相属。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燕蝠尘中,鸡虫影里,见了还追逐。山间林下,几人真个幽独。 谁似当日严君,故人龙衮,独抱羊裘宿。试把渔竿都掉了,百种千般拘束。两岸烟林,半溪山影,此处无荣辱。荒台遗像,至今嗟咏不足。
杨万里: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张轼:考子陵之言论风旨,亦非索隐行怪必欲长往而不返者。彼与光武少而想从,知其心度最为详也。以治谓光武欲为当时之治,则当时之治,则当时之人才固足办之,而无待乎已也。若欲进乎两汉之事,则又惧有未能信从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其尊礼之虚名,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宁不就之。
钱时:污浊成风,节廉道丧,鼓一世于浮竞之途,贪荣冒而不知耻,于是而有人焉脱身势利,高蹈林泉,优游恬退以终其身,虽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未必合圣人之中道,而风节凛凛足以激颓波,厉污俗,此严光、周党之徒,后世犹有取焉。
徐钧:故人风谊可态忘,辞禄无嫌故态狂。仁义一言非小补,此身何必佐岩廊。
郑锐:先生少与光武同学,熟知光武为人,其曰“差增于往”盖有以觇其衷,度其后居无何,后废子易,不能保骨肉之爱,而何有于微时一布衣交。此则揣摩未形之恶,捐弃生平之好,非君子长者事,而先生忍为之呼?
宋濂(《苍云轩铭》):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为尽力。子陵何隐而不出,既出而决去哉?盖光武察察自用,其后宰辅多不以礼退,子陵预知其如此,故决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旧之义。此子陵所以为高也。苟徒以隐为高也,孰不可为子陵哉?
方孝孺: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李昌祺:桐江连天兮秋水长,富春摩空兮烟树苍。客星兮寒芒,汉宫兮苔荒。彼争攀龙鳞兮铭勋旗常,此宁着羊裘兮垂纶沧浪。以足加腹兮忱故态之犹狂,亷贪立懦兮掲世之防。云台钓台兮其髙颉颃,二十八人兮图像已忘,先生万古兮岿祠堂。
何孟春:春观子陵与侯君房书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得书奏帝,帝有“狂奴故态”之哂,及幸其馆,抚腹之问,声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岂礼貌贤者之言也。子陵是时年亦已长矣,帝不以师友处子陵,而职谏议大夫之除,何哉?使子陵而职谏议大夫,不能一毫阿谀顺旨,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则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政归台阁,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群臣往往以非谶而见罢黜,将来之事废后易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时有死其职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职,非贤者所以爱其君之初意,去其君受职之余,孰与今日之不受之为全其节,而君臣之间两可无憾也哉!呜呼,此子陵之心也!
徐渭: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袁宏道:因山以为台,因水以为滩,因草以为丝,因木以为竿,因拙而辞世,因傲而弃官。严翁诚自知,刘叔亦难瞒。宁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郭子章:严光加足于帝腹,光忘帝之贵也;唐肃宗因李泌假寐,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帝自忘其贵也。布衣之遇天子,至光、泌极矣。桐江一丝,扶汉九鼎;历佐四圣,而后脱屣。光、泌所以报人主者,亦至矣哉。
王夫之:矫厉亢爽,耻为物下,道非可隐,而自旌其志,严光、周党是也。
李光地:①古来高隐人,不尽是忘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严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②子陵高风峻节,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厉天下之人心。东汉末,宦祸、党锢频兴,而赴仁蹈义者,视死如归,子陵之力也。
展开阅读全文 ∨
纠错
后世遗迹
严子洞位于汝州市蟒川乡十字路村南,严子河(现误为燕子河)东岸富春山(群众叫东山)脚下,有一石洞,高、宽约3米,深约4米,大洞往里延伸为一小洞,深约3米,只可放物,不可住人。此洞曾为严光的隐居处。
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富春山面临严子河,传即子陵隐居处。山上有子陵洞(即严子洞),嘉庆七年(1802年)监生杨顺重修,并塑子陵像于其中。山下有小山,即钓鱼台也。”
今仍存洞内的石钟及洞口西侧的石井、煎药灶,洞后的炒药灶、放药杵处,及山下河边的钓鱼台等遗迹。
严光在此隐居期间,常为人消灾治病,其家乡流传着许多传说。人们为了尊敬他,称之为“严子爷”,并在洞前建祠奉祀、起庙会以示纪念,洞前的河流也被叫做严子河(现误写为“燕子河”)。
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富春山面临严子河,传即子陵隐居处。山上有子陵洞(即严子洞),嘉庆七年(1802年)监生杨顺重修,并塑子陵像于其中。山下有小山,即钓鱼台也。”
今仍存洞内的石钟及洞口西侧的石井、煎药灶,洞后的炒药灶、放药杵处,及山下河边的钓鱼台等遗迹。
严光在此隐居期间,常为人消灾治病,其家乡流传着许多传说。人们为了尊敬他,称之为“严子爷”,并在洞前建祠奉祀、起庙会以示纪念,洞前的河流也被叫做严子河(现误写为“燕子河”)。
展开阅读全文 ∨
您可能感兴趣...
文章点评...
作者
仲子陵
王毂
王鉴
吴存楷
陶梦桂
方太古
罗伦
吴殳
曹于汴
程本立
赵宽
陆应旸
易顺鼎
戴察
际智
程端礼
陆友仁
麻革
徐承烈
田艺蘅
刘树堂
鲁一同
黄佐
赵国璧
卢儒
张英
车万育
黄钧宰
王用宾
章惇
刘鲁风
翁绶
杜旟
姜宸英
徐积
刘章
费昶
陆厥
谢安
司马懿
杨方
祖台之
束皙
周弘让
吴应箕
朱昂
何孟雄
郭麟
孙良器
守端
李昪
徐侨
卞之琳
柳浑
张昱
谢谔
清顺
郑振铎
丰子恺
郁达夫
王琮
孔德绍
吴兆骞
周亮工
王轩
周文雍
护国
沈辽
虞仲文
赵延寿
张协
刘献廷
虞骞
任昉
谢瞻
赵功可
陆可教
吴莱
刘弗陵
张打油
道璨
陈烈
朱鹤龄
陈季
袁正真
张简
邢昉
马祖常
詹时雨
大食惟寅
范康
厉声教
陈高
沈钦圻
朱一是
唐圭璋
习近平
陈郁
赵淇
严识玄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