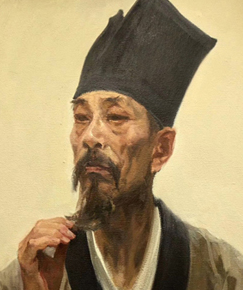齐州北水门记
济南多甘泉,名闻者以十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其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为门以泄之。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至是,始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因其故门,累石为两涯,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中置石楗,析为二门,扃皆用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其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备库副使驻泊都监张如纶,右侍禁兵马监押伸怀德。二人者,欲后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来请书,故为之书。是时熙宁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知齐州军事曾巩记。
纠错
鉴赏
纠错
曾巩虽以文坛大家名扬四海,却一生坎坷,仕途崎岖。既使“慨然有志于天下事”,终因“晚乃得仕”,又“不肯苟合”而空负王佐之材,满腹经纶只能“施设止于一州”。由嘉祐二年 (1057) 及进士第,曾巩便累迁外任。先后转徙太平、越、齐、襄、洪、福、明、毫、沧凡九州。所任或参军、或通判、或知州军州事,无一处不留下政声。其间,虽也有金殿应制,升降品阶的时机,但无论馆阁编校、侍郎都尉、中书舍人,终究是“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曾巩行状》) 而未起大用。及至晚年,朝廷忙于加官晋爵,怎奈曾子固已为路府州县耗尽了心力,竟于元丰六年(1083) 四月卒于江宁。可叹一代英才,文坛巨匠却将不少时光与精力空酒在艰辛的旅途跋涉之中。然而曾子十年外任,既让九州黎民得福,亦使北宋文苑有幸,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治理州邑、澄清风俗、灭害除患、造福民生的佳话轶闻。其中凡能以文字华章传阅后人的,则多是曾氏大家手笔之佼佼者。即使是记叙州府琐事,品评世态民情,志铭小大碑记的短篇,亦显得朴实自然,简明洁净而精巧隽永。《齐州北水门记》正是其中一篇不奇不崛,文义流畅,笔墨真淳疏秀的叙记小品,唯细读精微,方能体察其味无穷。
熙宁五年 (1072) 曾巩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军州事,至熙宁六年的夏秋间转任襄州,供职不到二年。然而曾子固在齐州的政绩显彰,似为历任九州之首。其中又以除暴平盗,兴修水利两项斐然成就,尤可证其“所治常出人上”( 《曾巩行状》)。《宋史》本传称他“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所谓鉴辟悍强喜攻劫之齐俗,惩豪宗大姓于敛手,以至齐境“外户不闭”; 而“发民浚河“能”括其隐漏”、“省费数倍”; 又“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均见《宋史》本传) 曾巩在齐州任上尤为地方百姓所爱戴,以至罢职离任之时,“州人绝桥闭门遮留”,曾巩只能“乘夜间乃得去。”(《曾巩行状》) 而曾氏本文所记,正是由他倡议并主持的修建城北水门,以绝水患的始末。
全篇可读为三节。首节申述昔以“荆苇为蔽,纳土于门”而“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虽防水患而害不能绝; 二节叙记北水门兴筑之经过,称赞水门成而“人无后虞,劳费以熄”; 末节指明水门修筑的时间,工程负责官员以及曾巩亲撰此记的原由与目的。
作为一篇专门记述工程兴筑的史实以刻石纪念的文章,虽并无成法,若在俗手则往往以歌功颂德者多。曾巩此文的运笔之妙恰背其道,以事不夸饰,辞不溢美,事在物在,褒贬自得的行文,将修建水门写得明白详实,层次清晰。作者精于记述,语言质朴,而评论客观又不夹杂己念,使全文顺妥自然,题旨鲜明。本篇在艺术上以巧用对比,自然平实; 举重若轻,意到笔随; 以及首尾一谐一庄相映成趣为其特色,写来游刃自如,令人回味。
曾巩此文叙事写实,很注意水门修筑前后的对比,短文的主要篇幅即用于表述这种比勘之惊人处。而运笔又极简洁平静,虽不直指利弊,实际已暗寓褒贬。作者文思缜密,写来有条不紊,从水门的耗用工料入手,历数其位置形制、治患功用、花费时间、直接效益,主事者之态度,逐一比照。而行文似不着意于“比”字,只是一心记述水门前后的实况实情。先指明所用材料的不同:旧时排水仅用“荆苇”与“土”疏道,其简陋而又不能经久显然,而水门俨然是一规划长远的工程,“买石”构筑,“垒石涯”、“置石楗”,唯“门,扃皆用木”。木石与“荆苇”与“土”差别悬殊,两相比较其优劣已见端倪。继而写旧时唯依“北城之下”自然形成的疏道,“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堵塞门洞以求“蔽”,完全是被动消极的方法,使“疏为门”徒有虚名;而新建的水门,工程设计井然有据,“因其故门垒石为两涯”,扩大和加深了原门洞处之疏道,使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排水泄洪的能力亦大大增强。又“置石楗”于水道之中,因势利导、分水巧妙,且能“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在水患面前人已掌有主动权。至此疏道与水门之利弊或已见分晓。这二个对比是本文的笔墨重彩处,文字也简明生动。新水门的设计、位置、构造、“深广”,规模一一说清了,旧疏道的诸项弊端也就个个显露出来。于是水门与疏道防治水患的实际功用也立刻形成鲜明的对照:“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只能是“以防外水之人”;至于“防”、“蔽”的是否坚实可靠,“外水”是否会由此成灾,作者一概不提。可见旧疏道的防水害,并不能让齐州城内外高枕无忧。至于新筑水门的立见其效:“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确是有目共睹。事物的自身说法实在是最有力的。由此,作者更得出不同的结论: 旧疏道必然“既费坚完”,使人提心吊胆,兼以年年相沿旧习,“又劳且费”。而新水门的一劳而永逸,不但使“人无后虞”,更收“劳费以熄”之益,无疑一举多得。作者在文思运笔之中,处处对比,又不特意喧染:语句始终平实、冷静、流畅。写旧疏道语少而不指贬,叙新工程更要言不烦,条理清晰。虽褒扬其事却无一处不是客观如实的记载。描述新水门的机巧处并不溢美,点破旧时的弊端处亦无夸饰。所谓“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人无后虞,劳费以熄”二句,是全篇仅有的从字面上涉及修筑水门利弊的评语。作者仍是客观地从水患能否根除,物钱耗费是否加重民力落笔,用词精辟而自然,毫无刻意雕琢之嫌。
所谓旧疏道的徒有其名,治水患用旧法相沿成习,而齐州城的水患终不能根绝;对比于新水门的构筑精巧实用,立竿见影,“人无后虞”。曾巩在布局谋篇时的缜密与匠心,从平实自然的记叙中显现出来。对比手法的效果虽在一种细微的体察之中,但无时无刻不有,给人的印象极深。以水门修筑所需的工时人力而言,作者只明写为一长一短的两句:“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以及另一句尾的“僦民为工”。实际上洋溢着曾巩对军民上下齐心合力兴筑水门的赞叹。“至是始”三字,虽指筑水门的行动自曾巩到任才倡议、才筹划、才实行,然而“至”字无形中揭示了曾巩之前任对治理水患,大多持敷衍,等待或搪塞的态度。作者笔触看似平实,实际上凡紧要处都暗寓胸臆,论说议评亦藏在字里行间。举如“常取”二字,明指旧习相延,何尝不是点斥历届前任对待水害,总囿于不求根治,劳民伤财的保守与短视。
曾巩的精于叙述,尤以“记”体见长。古人所谓“勘灾、浚渠、筑塘,语务严实,必举有益于民生者,始矜重不流于佻。”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 曾氏此文能举重若轻,结构全文时便故意将一件“有益于民生”的水利工程,写的平淡无奇,小而又小。作者原可就旧疏道的“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与新水门的“人无后虞,劳费以熄。“大做文章。但曾子固对疏道与水门的议论、评价亦不过仅此而已,并不借题发挥。笔下行文力求大事小写,而文中寓意又总是小中见大。“荆苇”、“纳土”,以“蔽”求“防水”,寥寥数语,便将防患水害这件于州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事,只系于一条以荆条、芦苇遮挡,堆土堵门的所谓“疏道”。担戴干系偌大,落在实处偌小,使文章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人一种无形的警策。作者常信笔拈来,而“语务严实”,又能坚持文辞“矜重而不流于佻”,无怪乎意到笔随,有潜移默化之功。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为例。曾巩极善理财。他知齐州,倡议并主持兴筑北水门工程,却不借机盘剥百姓,而是以“库钱买石”,取之于民又用于民,理当如此。此处避开“库钱”的收缴与使用这二大关键,轻灵地用“库钱买石”四字悄然地带过,既使短文内容集中,又使与题旨相关的人事,都在字面之外给读者以启迪。所谓“意到笔到”,而意之褒贬又往往是小中见大,别有洞天。可见曾巩撰著“记”体文的笔法,堪称艺术风格中的一绝。
本文以记事写实为主,虽暗寓褒贬,主旨并不在议论。所以曾子固为避免平实自然、简洁明晰容易带来的呆板、枯燥、干涩的弊病,在通篇几乎白描的同时,于文章的首尾巧作变化。用一谐一庄的笔触,使行文有起伏波澜,顿时妙趣横生。这种既庄重又活泼的记述与描写,既紧扣主题,又使全篇由始至终成为一个整体。
短文的主旨是记述北水门的兴筑及其对治理水患的功用。作者一落笔却是描写“济南多甘泉”。“家家有流水”的奇观。宋时齐州治所即在济南,而济南历来以水多名泉而闻名。素有“山川甲齐鲁、名泉甲天下”之盛誉。篇首作者即以浓墨勾勒济南府城的自然水势: 水丰泉多,“名闻者以十数”,以至“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济南以“泉城”名天下,正得益于水。这段描写堪称铺垫,为水患的形成,指出地理形貌上的特征与原因。至于明确地指出“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且“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则说明水门之兴筑势在必行。记叙文易陷于单调无味,而历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所以篇首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作者以生动优美的笔触,丰富了文章的艺术内涵,增加了下文申述水门兴建前后对比的鲜明与信实的依据。起笔即翻波折。“谐”字在先,无疑使全文增添了可读性与感染力。
至于结篇的“庄”,是指曾巩撰记时庄重严肃的态度。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曾巩,从倡议到主持兴建直至峻工使用均了如指掌。但文中并无涉及自身的一句褒辞。《曾巩墓志》称赞他每到一州“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后理颓弊,正风俗,皆曲折就绳墨”。可见曾巩守土为官的清廉、志向和政声。作者不没人善。文末注明监办水门工程的曹吏二人名姓。曾氏虽一方之长,却无居功之念,亦可见曾子固落笔的庄重诚恳、记文的信实可靠。“庄”字在后,于平实自然之中。越发体现曾巩的品行与心志。全文以首尾的一谐一庄互映成趣,同时又成为作者巧用对比之法、善于举重若轻的陪衬,读来并无枝蔓游离之感。
熙宁五年 (1072) 曾巩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军州事,至熙宁六年的夏秋间转任襄州,供职不到二年。然而曾子固在齐州的政绩显彰,似为历任九州之首。其中又以除暴平盗,兴修水利两项斐然成就,尤可证其“所治常出人上”( 《曾巩行状》)。《宋史》本传称他“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所谓鉴辟悍强喜攻劫之齐俗,惩豪宗大姓于敛手,以至齐境“外户不闭”; 而“发民浚河“能”括其隐漏”、“省费数倍”; 又“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均见《宋史》本传) 曾巩在齐州任上尤为地方百姓所爱戴,以至罢职离任之时,“州人绝桥闭门遮留”,曾巩只能“乘夜间乃得去。”(《曾巩行状》) 而曾氏本文所记,正是由他倡议并主持的修建城北水门,以绝水患的始末。
全篇可读为三节。首节申述昔以“荆苇为蔽,纳土于门”而“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虽防水患而害不能绝; 二节叙记北水门兴筑之经过,称赞水门成而“人无后虞,劳费以熄”; 末节指明水门修筑的时间,工程负责官员以及曾巩亲撰此记的原由与目的。
作为一篇专门记述工程兴筑的史实以刻石纪念的文章,虽并无成法,若在俗手则往往以歌功颂德者多。曾巩此文的运笔之妙恰背其道,以事不夸饰,辞不溢美,事在物在,褒贬自得的行文,将修建水门写得明白详实,层次清晰。作者精于记述,语言质朴,而评论客观又不夹杂己念,使全文顺妥自然,题旨鲜明。本篇在艺术上以巧用对比,自然平实; 举重若轻,意到笔随; 以及首尾一谐一庄相映成趣为其特色,写来游刃自如,令人回味。
曾巩此文叙事写实,很注意水门修筑前后的对比,短文的主要篇幅即用于表述这种比勘之惊人处。而运笔又极简洁平静,虽不直指利弊,实际已暗寓褒贬。作者文思缜密,写来有条不紊,从水门的耗用工料入手,历数其位置形制、治患功用、花费时间、直接效益,主事者之态度,逐一比照。而行文似不着意于“比”字,只是一心记述水门前后的实况实情。先指明所用材料的不同:旧时排水仅用“荆苇”与“土”疏道,其简陋而又不能经久显然,而水门俨然是一规划长远的工程,“买石”构筑,“垒石涯”、“置石楗”,唯“门,扃皆用木”。木石与“荆苇”与“土”差别悬殊,两相比较其优劣已见端倪。继而写旧时唯依“北城之下”自然形成的疏道,“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堵塞门洞以求“蔽”,完全是被动消极的方法,使“疏为门”徒有虚名;而新建的水门,工程设计井然有据,“因其故门垒石为两涯”,扩大和加深了原门洞处之疏道,使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排水泄洪的能力亦大大增强。又“置石楗”于水道之中,因势利导、分水巧妙,且能“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在水患面前人已掌有主动权。至此疏道与水门之利弊或已见分晓。这二个对比是本文的笔墨重彩处,文字也简明生动。新水门的设计、位置、构造、“深广”,规模一一说清了,旧疏道的诸项弊端也就个个显露出来。于是水门与疏道防治水患的实际功用也立刻形成鲜明的对照:“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只能是“以防外水之人”;至于“防”、“蔽”的是否坚实可靠,“外水”是否会由此成灾,作者一概不提。可见旧疏道的防水害,并不能让齐州城内外高枕无忧。至于新筑水门的立见其效:“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确是有目共睹。事物的自身说法实在是最有力的。由此,作者更得出不同的结论: 旧疏道必然“既费坚完”,使人提心吊胆,兼以年年相沿旧习,“又劳且费”。而新水门的一劳而永逸,不但使“人无后虞”,更收“劳费以熄”之益,无疑一举多得。作者在文思运笔之中,处处对比,又不特意喧染:语句始终平实、冷静、流畅。写旧疏道语少而不指贬,叙新工程更要言不烦,条理清晰。虽褒扬其事却无一处不是客观如实的记载。描述新水门的机巧处并不溢美,点破旧时的弊端处亦无夸饰。所谓“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人无后虞,劳费以熄”二句,是全篇仅有的从字面上涉及修筑水门利弊的评语。作者仍是客观地从水患能否根除,物钱耗费是否加重民力落笔,用词精辟而自然,毫无刻意雕琢之嫌。
所谓旧疏道的徒有其名,治水患用旧法相沿成习,而齐州城的水患终不能根绝;对比于新水门的构筑精巧实用,立竿见影,“人无后虞”。曾巩在布局谋篇时的缜密与匠心,从平实自然的记叙中显现出来。对比手法的效果虽在一种细微的体察之中,但无时无刻不有,给人的印象极深。以水门修筑所需的工时人力而言,作者只明写为一长一短的两句:“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以及另一句尾的“僦民为工”。实际上洋溢着曾巩对军民上下齐心合力兴筑水门的赞叹。“至是始”三字,虽指筑水门的行动自曾巩到任才倡议、才筹划、才实行,然而“至”字无形中揭示了曾巩之前任对治理水患,大多持敷衍,等待或搪塞的态度。作者笔触看似平实,实际上凡紧要处都暗寓胸臆,论说议评亦藏在字里行间。举如“常取”二字,明指旧习相延,何尝不是点斥历届前任对待水害,总囿于不求根治,劳民伤财的保守与短视。
曾巩的精于叙述,尤以“记”体见长。古人所谓“勘灾、浚渠、筑塘,语务严实,必举有益于民生者,始矜重不流于佻。”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 曾氏此文能举重若轻,结构全文时便故意将一件“有益于民生”的水利工程,写的平淡无奇,小而又小。作者原可就旧疏道的“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与新水门的“人无后虞,劳费以熄。“大做文章。但曾子固对疏道与水门的议论、评价亦不过仅此而已,并不借题发挥。笔下行文力求大事小写,而文中寓意又总是小中见大。“荆苇”、“纳土”,以“蔽”求“防水”,寥寥数语,便将防患水害这件于州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事,只系于一条以荆条、芦苇遮挡,堆土堵门的所谓“疏道”。担戴干系偌大,落在实处偌小,使文章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人一种无形的警策。作者常信笔拈来,而“语务严实”,又能坚持文辞“矜重而不流于佻”,无怪乎意到笔随,有潜移默化之功。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为例。曾巩极善理财。他知齐州,倡议并主持兴筑北水门工程,却不借机盘剥百姓,而是以“库钱买石”,取之于民又用于民,理当如此。此处避开“库钱”的收缴与使用这二大关键,轻灵地用“库钱买石”四字悄然地带过,既使短文内容集中,又使与题旨相关的人事,都在字面之外给读者以启迪。所谓“意到笔到”,而意之褒贬又往往是小中见大,别有洞天。可见曾巩撰著“记”体文的笔法,堪称艺术风格中的一绝。
本文以记事写实为主,虽暗寓褒贬,主旨并不在议论。所以曾子固为避免平实自然、简洁明晰容易带来的呆板、枯燥、干涩的弊病,在通篇几乎白描的同时,于文章的首尾巧作变化。用一谐一庄的笔触,使行文有起伏波澜,顿时妙趣横生。这种既庄重又活泼的记述与描写,既紧扣主题,又使全篇由始至终成为一个整体。
短文的主旨是记述北水门的兴筑及其对治理水患的功用。作者一落笔却是描写“济南多甘泉”。“家家有流水”的奇观。宋时齐州治所即在济南,而济南历来以水多名泉而闻名。素有“山川甲齐鲁、名泉甲天下”之盛誉。篇首作者即以浓墨勾勒济南府城的自然水势: 水丰泉多,“名闻者以十数”,以至“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济南以“泉城”名天下,正得益于水。这段描写堪称铺垫,为水患的形成,指出地理形貌上的特征与原因。至于明确地指出“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且“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则说明水门之兴筑势在必行。记叙文易陷于单调无味,而历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所以篇首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作者以生动优美的笔触,丰富了文章的艺术内涵,增加了下文申述水门兴建前后对比的鲜明与信实的依据。起笔即翻波折。“谐”字在先,无疑使全文增添了可读性与感染力。
至于结篇的“庄”,是指曾巩撰记时庄重严肃的态度。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曾巩,从倡议到主持兴建直至峻工使用均了如指掌。但文中并无涉及自身的一句褒辞。《曾巩墓志》称赞他每到一州“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后理颓弊,正风俗,皆曲折就绳墨”。可见曾巩守土为官的清廉、志向和政声。作者不没人善。文末注明监办水门工程的曹吏二人名姓。曾氏虽一方之长,却无居功之念,亦可见曾子固落笔的庄重诚恳、记文的信实可靠。“庄”字在后,于平实自然之中。越发体现曾巩的品行与心志。全文以首尾的一谐一庄互映成趣,同时又成为作者巧用对比之法、善于举重若轻的陪衬,读来并无枝蔓游离之感。
展开阅读全文 ∨
您可能感兴趣...
-
凝香斋
每觉西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诸侯。一尊风月身无事,千里耕桑岁有秋。云水醒心鸣好鸟,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烟细细临黄卷,疑在香炉最上头。...
- 2
-
甘露寺多景楼
欲收嘉景此楼中,徒倚阑干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餐风。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 3
-
读书
吾性虽嗜学,年少不自强。所至未及门,安能望其堂。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最自忆往岁,病躯久羸尫。呻吟千里外,苍黄值亲丧。母弟各在无,讣归恐惊惶。凶祸甘独任,危形载孤艎。...
- 1
-
西楼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 4
-
游信州玉山小岩记
去县治所东南二十五里,有山秀特卓诡,介然出于群峰之表。下有浮图,幽邃冲静,栋宇朴约,无彩饰刻镂,而与俗绝远。游其间,真若排阊阖,登 ...
- 803
-
洪渥传
洪渥,抚州临川人。为人和平。与人游,初不甚欢,久而有味。家贫。以进士从乡举,有能赋名。初进于有司,连辄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驰 ...
- 323
-
冬夜即事
印奁封罢阁铃闲,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仓廪实,邑尨无警里闾安。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门霿凇寒。闻说丰年从此始,更回笼烛卷帘看。...
- 3
-
谒李白墓
世间遗草三千首,林下荒坟二百年。信矣辉光争日月,依然精爽动山川。曾无近属持门户,空有乡人拂几筵。顾我自惭才力薄,欲将何物吊前贤。...
- 0
-
雨中王驾部席上
鸠呼连日始成阴,薄雨聊宽望岁心。浴雁野塘新浪细,藏鸦宫柳嫩条深。春寒巧放花迟发,人老嗟辞酒满斟。英隽并游知最幸,名园偷暇更追寻。...
- 2
-
南轩竹
密竹娟娟数十茎,旱天萧洒有高情。风吹已送烦心醒,雨洗还供远眼清。新笋巧穿苔石去,碎阴微破粉墙生。应须万物冰霜后,来看琅玕色转明。...
- 0
文章点评...
诗文类型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作者
阅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