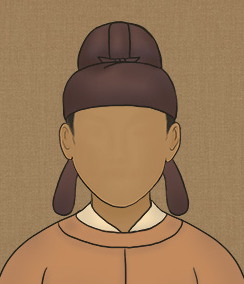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下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榜来召者。全素曰:“礼闱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
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捽之者,拽倒者,杻枷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入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部分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
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碨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犊,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捡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出身,其后三年衣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犊!”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迟,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羡而泣者不可胜纪。既出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科命甚薄,突明即归,得不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不应。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
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忍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手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
曰:“然则何以言事?”
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
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毕,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魇不寤矣。”
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
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
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
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
全素曰:“固所愿也。”
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计当寝床,有抽瓦拆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
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椊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拽于堂前,以绳缚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
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
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
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生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静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苦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
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言语切切。沙门三人当窗读《八阳经》,因此不敢逼。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投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己啼矣。二吏曰:“事毕矣,送君去。”
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
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
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乃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一端,足可以诫其知进而不知退者。
译文及注释
纠错
译文:
吴全素,是苏州人。他被举荐参加科举考试,连着五次没有考中。
唐元和十二年,他寄住在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里,他已经睡了,看见两个穿白衣的人拿着文书,像贡院拿着来召唤人去考试的。
全素说:“礼部举行考试,什么科目在什么时间举行,是有定期的,何须烦劳你们夜间来召唤?”那两个使者坚决邀请,吴全素没办法,就下床跟着他们走。
不知不觉间他们走过子城、走出开远门二百步,向正北走,有条两尺来宽的路,这以外满眼是很深的泥淖。只见男人女人,有被揪着的,被拉倒在地的,披枷戴铐的,有和尚、道士,有用袋子套住头的、两手被反绑在身后的、被胡乱地驱赶着走的。
几百人都在泥淖中踉跄行进,只有吴全素在平路上,走了好几里,他们走进城,看见官府,排列在一起的有一千多人,带刀的军士官吏,分队押解他们,大致五十个人一批,按批走过,全素分在第三批中。
那官府的正衙有座大殿。当中摆着坐榻,有一个人穿着红袍坐着,他的左右站着几十名官吏,有衙吏在点名,接着便判处交付主管牢狱的、有交付给磨狱的,有交付给矿狱的,有交付给汤狱的,有交付给火狱的,也有交付审理的。全素听到这些人被交付给各种监狱、才知道自己死了。
唐元和十二年,他寄住在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里,他已经睡了,看见两个穿白衣的人拿着文书,像贡院拿着来召唤人去考试的。
全素说:“礼部举行考试,什么科目在什么时间举行,是有定期的,何须烦劳你们夜间来召唤?”那两个使者坚决邀请,吴全素没办法,就下床跟着他们走。
不知不觉间他们走过子城、走出开远门二百步,向正北走,有条两尺来宽的路,这以外满眼是很深的泥淖。只见男人女人,有被揪着的,被拉倒在地的,披枷戴铐的,有和尚、道士,有用袋子套住头的、两手被反绑在身后的、被胡乱地驱赶着走的。
几百人都在泥淖中踉跄行进,只有吴全素在平路上,走了好几里,他们走进城,看见官府,排列在一起的有一千多人,带刀的军士官吏,分队押解他们,大致五十个人一批,按批走过,全素分在第三批中。
那官府的正衙有座大殿。当中摆着坐榻,有一个人穿着红袍坐着,他的左右站着几十名官吏,有衙吏在点名,接着便判处交付主管牢狱的、有交付给磨狱的,有交付给矿狱的,有交付给汤狱的,有交付给火狱的,也有交付审理的。全素听到这些人被交付给各种监狱、才知道自己死了。
他看见同一批的四十九个人都点名交付完毕,只有自己站在那里,于是问那里的人说:“值衙的是个什么官?”
回答说:“是判官。”
全素便诉告说:“我谨慎地履行儒家的为人之道,年寿、俸禄没享用完,不应该死。”
判官道:“阴间的文书,一件件写得明明白白,我们是根据簿籍的记载来追捕的,难道能由得你瞎说。”
全素说:“我确实知道自己的寿命没有完尽,现在请求核对记录寿命的簿册。”
判官于是叫人拿来吴郡的户籍,找到吴全素的姓名,上面写着:“元和十三年考中明经科,那以后还有三年阳寿,也不会做官拿俸禄。”
判官说:“人世的三年,只是眨眼之间,并且又无俸禄可享,何必回去!回到人间,又马上要来,白白地烦劳我们办文书。”
全素说:“我辞别双亲五年了,能回去就是好事,何况取得功名后,还有三年的阳寿,拜求您怜悯与体谅。”
判官说:“让你回去吧。”
并且告诫带领他回去的人说:“这个人的命薄,应该让他赶快走。稍微拖延,天就要亮了。”
带领的人接受了命令,立即跟他一起动身。他们走出殿门外,羡慕全素而流泪的人,多得记不尽。出了城,再没看到泥淖了。
又走到开远门,那两个官吏对全素说:“您的命很薄,天一亮便回不成了,你听见判官说的话吗?我俩都穷,送我们各五十万钱,就不必担心了。”
全素说:“我离家乡远,又贫穷,怎么能弄到这么多钱?”
官吏说:“你姨母的丈夫,住在宣阳里,在户部做官,家里很富,只要向他说一声,钱就可到手。”
大家一同走到姨父家,那两个官吏不肯走上台阶,全素进屋去告诉情况。
姨父家正在吃煎饼,全素走到灯前拱手行礼说:“阿姨万福。”姨母不理睬他。
又说:“姨父安和。”姨父又不答话。全素就用手把灯罩起来,整间屋都暗了。
姨父说:“为什么不丢点煎饼?我们夜里吃香的东西,鬼神便该恼恨我们了。”
全素既对他们不理睬自己感到不满,又被姨父当作鬼神看待,心中更加愤恨他们。
一个奴婢拿着饼吃,正面对着他,于是便举手打了她一个耳光,那奴婢应手倒地昏迷不醒,姨父家的人争着来拉扯她的头发,向她脸上喷水,呼喊了好久,才醒过来。
全素既然没法告诉他要钱的事,便走下台阶,问两个官吏。
他们说:“本该这样,你没有复活,不是鬼是什么?鬼说话,人是听不见的,你用手把灯罩起来,打了奴婢的耳光,确实足够使他们惊骇了。”
全素说:“既然这样,那么我怎么去讲要钱的事?”
回答说:“把我们的唾沫涂在人家的大门上,全家人会睡;涂在人家的中门上,门里的人会睡;涂在堂屋的门上,整个堂屋的人会睡。你可以用手承接我们的唾沫,去涂堂门。”
全素捧起两手,两个官员交替向他手里吐唾沫。不一会,他两手捧着去涂堂门,才涂完,满屋的人打起呵欠,催着收拾碗筷,便进去睡觉了。
两位官吏说:“你现在可以去了,站在窗边三尺的位置说话就行了。切记不要靠近床榻,用手摇动床榻,人就做恶梦不醒了。”
全素依照他俩说的去讲要钱的事,他姨母惊醒起来、流着泪对丈夫说:“全素晚上回来睡觉,为什么突然死了?现在他托梦求钱,说是要送人。该怎么办?”
她丈夫说:“你心里悲伤,惦念外甥,偶然做了个恶梦,哪值得就相信呢!”
姨母又睡下,又做梦,惊骇而起,流着泪、在柜子里找纸,恰巧有二百张,便叫人立刻剪成纸钱烧了,火熄灭,一千贯钱仿佛就在地上了。
那两个官吏对全素说:“钱的数量多,我们根本拿不动,但您是活人有力气,能够全部拿起来。请你背起这些钱,送去寄存起来。”
那两个官吏对全素说:“钱的数量多,我们根本拿不动,但您是活人有力气,能够全部拿起来。请你背起这些钱,送去寄存起来。”
全素起初认为这难以办到,试着用两只手往上提,用肩扛起它,巍峨耸立,极高极高,其实很轻。
于是两位官吏引着他,把钱寄存在介公庙,庙里的神主穿着紫袍,腰间围着金带,命令小吏把钱收下。
寄完钱,两位官吏说:“您的还生是一定的了,是想马上回去,还是看点什么再回去?现在我们去捉拿一个人,送他去投胎,能稍微看一下吗?”
全素说:“原来是我所希望的。”
于是领着他进了西市绢行南边尽头的一户人家,那人家灯火辉煌,家人在呜呜地哭泣,有几个和尚对着门在念经,满屋香烟缭绕,两个官吏不敢近前,于是从堂屋的后檐登上屋,估计对着睡床,又抽去屋瓦,拆开椽子,开了个大洞。
从洞中看下去,一个老人气息奄奄,相对哭泣的人围着他的床。
一个官吏从怀里拿出绳索,有指头那么粗、二丈多长,他叫全素坐好,拿着绳索的一头,把另一头从洞中放下去,告诫全素说:“我马上去捉拿那个人,一捉来,你应该拉绳索。”
那官吏就下到房里,用右手揪住老人,用左手拉动绳索。
全素急忙把老人拉了上来,拖在堂前,用绳索像捆囚犯似的把他绑起来。两个官吏轮换着把他背了出去,相互商量说:“哪儿有最大的屠宰案桌?”其中的一个说:“布政坊十字街南边王家的屠宰案桌最大。”
说完便一起到那里去了。走到那里,两人官吏把老人丢在屠宰案桌上,他俩脱下衣衫缠在身上,轮换着上去推转扑打,老人叫苦,那声音凄惨感人。
全素说:“他如果有罪,应该依法受刑罚;你们这样干,也是不合法的;如果没有罪,为什么折磨他?”
两个官吏说:“到这时候你才提出问题,我们感到惊讶。凡是有善功清德,该升天堂的人,有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接他去,这种人我们怎么能见到?如果有重罪和肮脏丑恶行径,该打入地狱的人,由牛头奇鬼带着铁叉枷铐来捉拿他,这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见到?”
“这个老人没有升入天堂的福份,又没有下地狱的罪行,虽然能洁身自好,但没有离开尘俗,只是保持清白,没有污点。这个身子既然舍去了,只应该投胎去变成另一个男人。当地方官计算好好的时候,他母亲已怀孕了,这个生命已经结束,那个生命应该诞生。现在如果不把他搓揉扑打,让那妇人怎么能生他呢?”
于是,又用力揉搓扑打,确实感到老人的躯体渐渐缩小。不一会躯体像只拳头那么大,肢体,眼耳口鼻,没有不像老样子的。于是慢慢地提着他。他们走过子城大胜业坊,沿着南方向直下再东回,在第二条小巷的北壁,走进第一户人家。
那家也是灯火辉煌,人们在小声说话。有两个和尚,对着窗子念《八阳经》。
这两个官吏不敢走近和尚,直接走上台阶,看见堂屋的门斜掩着,一个官吏提着老人,向堂屋丢去,似乎刚落到床上,婴儿已经啼哭了。
一个官吏对全素说:“我们的公事办完了,送您回去。”
他们又一起走进永兴里的旅舍,走进卧房,房里还黑,一点也看不见。两个官吏跟在全素的后面,于是推了他一把,大叫道:“吴全素!”
全素好像失脚坠落一样,苏醒后,头非常晕,很久心神才安定下来。这时官署报时的鼓声正在响,姨父从宣阳里骑马赶来。全素已经苏醒了,他的仆人对他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
全素坐轿子去宣阳姨父家休养,几天之后完全康复了。再从子城走进胜业坊那户生男孩的人家,前几天看见的那些情况,还清清楚楚地映在眼前。
他自认为考中明经科,也不值得荣耀,只想赶快回家去侍奉双亲。选定了动身的日期,有时因头晕走不成;有时因雇来的驴脚坏了;有时连日下雪;有时亲戚朋友来往;行期一再拖延,就逼近了考试的日期。全素进场考试,不再把以前想考中的希望放在心上。反而考中名动长安,全素大笑着辞别长安走了。
展开阅读全文 ∨
您可能感兴趣...
文章点评...
诗文类型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作者
阅读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