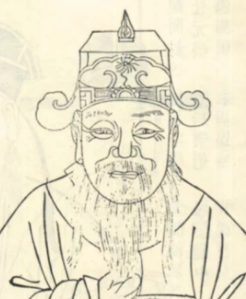天地间无久而不敝之物,唐、虞以前,遐哉邈乎,不可考矣。周、秦、汉、唐之世,迄今亦不获多见。其尚有存者,必其为人所注意,而人为存之也。非然,则历变故,经岁月,虽以金石之质,犹不能与天地以不敝,而况其为游观之所,亭台堂榭,风雨之所飘摇,鸟鼠之所剥啄,草木之所灌莽者乎?此周原鞠茂草,故宫离禾黍,铜驼在荆棘,昔人所悲,良有以也。善乎韩昌黎之言曰:“莫为之前,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凡废兴成毁之故,岂不以其人哉?庆历间,庐陵欧阳公实守是邦,为堂于蜀冈之上,负高眺远,江南诸山,拱揖槛前,若与堂平,故名。堂之左右,碧树参天,清风徐来,虽盛夏亦不知其为暑也。政成之暇,延四方之名俊,摘邵伯之荷蕖,传花饮酒,分韵赋诗,徜徉乎其中,不醉无归,载月而返,亦风流逸事也,心窃向往焉。及莅任维扬,访平山故迹,而荆榛塞道,荒葛罥涂,颓垣断栋,率剥烂不可支撑。去隆兴癸未周君淙重新之日不三十年,而凋残零落,遂至于此。吁嗟乎!自国家多故,戎马蹂?,先贤遗址,半为樵牧之区,骚人逸士,罕有过而问焉,又谁为保护而爱惜之,朴斫而丹雘之哉?无怪乎斯堂之旋圮也。呜呼!事以人传,以人传人,则传无穷。是役也,予何能辞其责?乃为之程土物,庀财用,卜日以鸠工。经始于客冬之九月,竣事于今春之二月。轩檐既启,江山欲来,仰挹松风,俯瞩流泉,二百年之壮观,一旦维新。既成,偕贤士大夫相与置酒而落之。游人士女,摩肩叠趾,聚而观者不下数千人,喁喁有更新之幸,则相与语曰:“太守奉天子命,以牧养小民,刑清政简,自宜有游观之美,以休其暇日。”予曰:不然。太守之新此堂也,岂徒快意适观,自乐其乐乎?夫黉宫斋舍,衅币告成,为多士庆之;比户穷檐,融风已熄,为兆民幸之。兹复汲汲于此堂者,毋亦以名贤作息之地,文章政事,昭人耳目,大有德于扬者,生既沾其泽,没亦宜馨其祀,将以此堂为栖神之所,设主于中,以见扬之人思公之深,爱公之至,太守之能顺民欲而新其堂,妥其灵也。所谓人所注意而人为存之者,其在斯乎?后之人嗣吾意而葺之,则可以久而不敝矣。时绍熙改元,岁在庚戌夏五上浣识。
扬州府志载:平山堂,在郡城西北五里。宋庆历八年,郡守欧阳修建,后刁约、周淙、郑兴裔相继新之。美泉亭,宋欧阳修建,郑兴裔重修。斗野亭,在江都邵伯镇,宋熙宁二年建。绍熙元年,郑兴裔更造于州城迎恩桥南。云山观,宋熙宁间,陈升之判扬州,创阁于子城上,曰云山。淳熙间,郑兴裔撤玉钩亭,增而大之,名云山观。
定远谨按:先忠肃公知维扬日,修废振坠,巨细毕举,平山堂特其一耳。他如疏濬漕河,以通飞挽,尤属经济大猷。国史、郡乘虽具载其事,多未详备。年谱载淳熙十五年事,注云:漕河即古刊沟,一名运河。公自有记,称“西南自仪真江岸东行四十里,至石人头,入江都县界。又十五里,至杨子桥。南自江都县瓜洲镇站船坞北行三十里,亦至杨子桥,二河始合。东转又北行六十里,入邵伯。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邮。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宝应。又北行至黄浦,接淮安山阳界,由清江浦入河”云云。惜乎遗编残缺,全文已不复可见,惟此平山堂记,如鲁灵光,岿然独存,捧读之下,不胜感慨系之,因附志于此。
译文及注释
纠错
译文
天地间没有长久而不毁坏的事物。唐虞以前的时代,实在是太过遥远,已经无从考证了。即使是周、秦、汉、唐这些朝代,到如今也鲜有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遗迹。而那些尚存的,必然是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并因此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经历种种变故和岁月的洗礼,即便是金石般坚硬的物质,也无法与天地同寿,更何况是那些供人游览观赏的地方,如亭台楼阁,它们遭受风雨的侵袭,鸟鼠的啄食,草木的覆盖,怎能不逐渐破败呢?这正是周朝原野长满茂盛的杂草,旧日宫殿长满禾黍,铜驼卧在荆棘丛中,古人所悲叹的,确实是有原因的。韩愈说得好:“没有前人的努力,即使美好也不能彰显;没有后人的传承,即使盛况也无法延续。”所有兴衰成败的缘由,难道不正是因为人吗?庆历年间,庐陵的欧阳修先生担任扬州太守,他在蜀冈之上建造了一座堂,这座堂背靠高山,视野开阔,江南的群山仿佛在堂前拱手作揖,仿佛与堂平齐,因此得名。堂的两旁,绿树参天,清风徐来,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感觉不到炎热。在政务之余,他邀请四方的名士俊才,采摘邵伯湖的荷花,传花饮酒,分韵赋诗,徜徉其中,不醉不归,乘着月色返回,这也是一段风流逸事,我心中十分向往。等到我赴任扬州,寻访平山堂的遗迹时,却发现道路被荆棘堵塞,荒草遍地,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几乎无法支撑。距离隆兴癸未年周君淙重新修缮还不到三十年,就已经凋残零落至此。唉!自从国家多难,战乱频仍,先贤的遗址多半变成了樵夫牧童的活动之地,文人墨客也很少有人来过问,又有谁来保护爱惜它们,为它们修缮装饰呢?难怪这座堂会这么快就倒塌了。唉!事物因人而传,人以事传,这样便能流传久远。对于这次修缮工作,我怎能推卸责任呢?于是我着手规划土地和物资,筹备资金,选择吉日召集工匠动工。工程从去年的九月开始,到今年的二月竣工。堂前的轩檐已经打开,仿佛江山都要涌进来,抬头可以挹取松间清风,低头可以观赏潺潺流水,这座有着二百年历史的壮观建筑,一时间焕然一新。竣工后,我邀请贤士大夫们一同前来置酒庆贺,并举行落成典礼。游人和士女们摩肩接踵,聚集观看的不下数千人,他们纷纷表示更新之后的喜悦,并相互议论说:“太守是奉了天子的命令来牧养百姓的,他刑罚清明,政事简约,自然应该有游览观赏的美景来让百姓在闲暇时得到休息。”我说:“不是这样的。太守之所以要重新修缮这座堂,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赏心悦目,自得其乐吗?学校校舍落成时,我们用牲畜的血来祭祀以告成功,是为了庆祝学子们的学业有成;家家户户,贫困的屋檐下,春风已经吹散了寒冷,这是为了百姓的幸福。而今我之所以急于修缮这座堂,也是因为它曾是名贤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的文章政事,昭彰于世人耳目,对扬州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世时,百姓得到了他们的恩泽;他们去世后,也应该让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我们将这座堂作为他们神灵栖息的地方,在中间设立神位,以此来表达扬州人民对他们的深切思念和崇敬之情。太守能够顺应民心而重新修缮这座堂,也是为了妥善安置他们的神灵。”这就是所说的“人们所关注并因此得到保护”的道理吧?后世的人如果继承我的意愿继续修缮它,那么它就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而不至于毁坏了。时间是在绍熙改元之年,庚戌年的夏五月初旬。
《扬州府志》记载:平山堂,位于郡城(即扬州城)的西北方向,距离城中心约五里地。这座堂是在宋朝庆历八年,由当时的扬州太守欧阳修主持修建的。后来,刁约、周淙、郑兴裔等人相继对其进行了修缮和更新。美泉亭也是由欧阳修在宋朝时建造的,而郑兴裔则对其进行了重修。至于斗野亭,它位于江都县的邵伯镇,始建于宋朝熙宁二年。然而,在绍熙元年,郑兴裔又在州城(扬州)的迎恩桥南侧重新建造了斗野亭。云山观则是在宋朝熙宁年间,由陈升之在担任扬州知府时,于子城之上创建的,起初称为云山阁。到了淳熙年间,郑兴裔拆除了原有的玉钩亭,将其扩建并更名为云山观。
定远(可能是作者或编撰者的谦称)谨按:我的先祖忠肃公(可能是指某位历史上的著名官员,具体身份需根据上下文或历史资料确定)在担任扬州知府期间,不仅修复了众多废弃破旧的建筑,还振兴了各项事业,无论大小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平山堂只是他众多政绩中的一项而已。除此之外,他还疏浚了漕河,以确保水路运输的畅通无阻,这更是他经济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举措。虽然国家史书和扬州的地方志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但很多细节仍然不够完备。在我的先祖的年谱中,淳熙十五年条目下有这样的注释:漕河即古代的刊沟,也称为运河。先祖曾亲自撰写文章记录此事,文中描述道:“从西南方向自仪真(今仪征)的江岸向东行四十里,到达石人头,便进入了江都县的界域。再前行十五里,便到了杨子桥。而从南面,自江都县的瓜洲镇站船坞向北行三十里,也同样到达杨子桥,这时两条河流开始汇合。接着向东再转北行六十里,便进入了邵伯。继续北行六十里,到达高邮。再北行四十里,到达界首,进入宝应县界。继续北行,直至黄浦,便与淮安山阳县界相接,随后通过清江浦汇入淮河。”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珍贵的文献多有残缺,全文已经难以复见。唯有这篇《平山堂记》,如同鲁国的灵光殿一般,虽然历经沧桑却仍然屹立不倒,独自保存至今。每当我手捧这篇记文细细品读时,都不禁感慨万千,因此特地将这些感慨附记于此。
注释
郑兴裔,宋朝人,曾任扬州知州,有政绩。
荆榛,灌木树丛。
涂,道路。
隆兴,南宋孝宗的年号。
周君淙,即周淙,曾在扬州驻军抗金。
朴斫而丹雘,修缮装饰。
圮,毁坏、坍塌。
天地间没有长久而不毁坏的事物。唐虞以前的时代,实在是太过遥远,已经无从考证了。即使是周、秦、汉、唐这些朝代,到如今也鲜有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遗迹。而那些尚存的,必然是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并因此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经历种种变故和岁月的洗礼,即便是金石般坚硬的物质,也无法与天地同寿,更何况是那些供人游览观赏的地方,如亭台楼阁,它们遭受风雨的侵袭,鸟鼠的啄食,草木的覆盖,怎能不逐渐破败呢?这正是周朝原野长满茂盛的杂草,旧日宫殿长满禾黍,铜驼卧在荆棘丛中,古人所悲叹的,确实是有原因的。韩愈说得好:“没有前人的努力,即使美好也不能彰显;没有后人的传承,即使盛况也无法延续。”所有兴衰成败的缘由,难道不正是因为人吗?庆历年间,庐陵的欧阳修先生担任扬州太守,他在蜀冈之上建造了一座堂,这座堂背靠高山,视野开阔,江南的群山仿佛在堂前拱手作揖,仿佛与堂平齐,因此得名。堂的两旁,绿树参天,清风徐来,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感觉不到炎热。在政务之余,他邀请四方的名士俊才,采摘邵伯湖的荷花,传花饮酒,分韵赋诗,徜徉其中,不醉不归,乘着月色返回,这也是一段风流逸事,我心中十分向往。等到我赴任扬州,寻访平山堂的遗迹时,却发现道路被荆棘堵塞,荒草遍地,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几乎无法支撑。距离隆兴癸未年周君淙重新修缮还不到三十年,就已经凋残零落至此。唉!自从国家多难,战乱频仍,先贤的遗址多半变成了樵夫牧童的活动之地,文人墨客也很少有人来过问,又有谁来保护爱惜它们,为它们修缮装饰呢?难怪这座堂会这么快就倒塌了。唉!事物因人而传,人以事传,这样便能流传久远。对于这次修缮工作,我怎能推卸责任呢?于是我着手规划土地和物资,筹备资金,选择吉日召集工匠动工。工程从去年的九月开始,到今年的二月竣工。堂前的轩檐已经打开,仿佛江山都要涌进来,抬头可以挹取松间清风,低头可以观赏潺潺流水,这座有着二百年历史的壮观建筑,一时间焕然一新。竣工后,我邀请贤士大夫们一同前来置酒庆贺,并举行落成典礼。游人和士女们摩肩接踵,聚集观看的不下数千人,他们纷纷表示更新之后的喜悦,并相互议论说:“太守是奉了天子的命令来牧养百姓的,他刑罚清明,政事简约,自然应该有游览观赏的美景来让百姓在闲暇时得到休息。”我说:“不是这样的。太守之所以要重新修缮这座堂,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赏心悦目,自得其乐吗?学校校舍落成时,我们用牲畜的血来祭祀以告成功,是为了庆祝学子们的学业有成;家家户户,贫困的屋檐下,春风已经吹散了寒冷,这是为了百姓的幸福。而今我之所以急于修缮这座堂,也是因为它曾是名贤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的文章政事,昭彰于世人耳目,对扬州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世时,百姓得到了他们的恩泽;他们去世后,也应该让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我们将这座堂作为他们神灵栖息的地方,在中间设立神位,以此来表达扬州人民对他们的深切思念和崇敬之情。太守能够顺应民心而重新修缮这座堂,也是为了妥善安置他们的神灵。”这就是所说的“人们所关注并因此得到保护”的道理吧?后世的人如果继承我的意愿继续修缮它,那么它就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而不至于毁坏了。时间是在绍熙改元之年,庚戌年的夏五月初旬。
《扬州府志》记载:平山堂,位于郡城(即扬州城)的西北方向,距离城中心约五里地。这座堂是在宋朝庆历八年,由当时的扬州太守欧阳修主持修建的。后来,刁约、周淙、郑兴裔等人相继对其进行了修缮和更新。美泉亭也是由欧阳修在宋朝时建造的,而郑兴裔则对其进行了重修。至于斗野亭,它位于江都县的邵伯镇,始建于宋朝熙宁二年。然而,在绍熙元年,郑兴裔又在州城(扬州)的迎恩桥南侧重新建造了斗野亭。云山观则是在宋朝熙宁年间,由陈升之在担任扬州知府时,于子城之上创建的,起初称为云山阁。到了淳熙年间,郑兴裔拆除了原有的玉钩亭,将其扩建并更名为云山观。
定远(可能是作者或编撰者的谦称)谨按:我的先祖忠肃公(可能是指某位历史上的著名官员,具体身份需根据上下文或历史资料确定)在担任扬州知府期间,不仅修复了众多废弃破旧的建筑,还振兴了各项事业,无论大小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平山堂只是他众多政绩中的一项而已。除此之外,他还疏浚了漕河,以确保水路运输的畅通无阻,这更是他经济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举措。虽然国家史书和扬州的地方志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但很多细节仍然不够完备。在我的先祖的年谱中,淳熙十五年条目下有这样的注释:漕河即古代的刊沟,也称为运河。先祖曾亲自撰写文章记录此事,文中描述道:“从西南方向自仪真(今仪征)的江岸向东行四十里,到达石人头,便进入了江都县的界域。再前行十五里,便到了杨子桥。而从南面,自江都县的瓜洲镇站船坞向北行三十里,也同样到达杨子桥,这时两条河流开始汇合。接着向东再转北行六十里,便进入了邵伯。继续北行六十里,到达高邮。再北行四十里,到达界首,进入宝应县界。继续北行,直至黄浦,便与淮安山阳县界相接,随后通过清江浦汇入淮河。”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珍贵的文献多有残缺,全文已经难以复见。唯有这篇《平山堂记》,如同鲁国的灵光殿一般,虽然历经沧桑却仍然屹立不倒,独自保存至今。每当我手捧这篇记文细细品读时,都不禁感慨万千,因此特地将这些感慨附记于此。
注释
郑兴裔,宋朝人,曾任扬州知州,有政绩。
荆榛,灌木树丛。
涂,道路。
隆兴,南宋孝宗的年号。
周君淙,即周淙,曾在扬州驻军抗金。
朴斫而丹雘,修缮装饰。
圮,毁坏、坍塌。
展开阅读全文 ∨
您可能感兴趣...
文章点评...
诗文类型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作者
阅读排行榜